


时间: 2023-10-29 17:32:36 | 作者: 产品中心
笔者对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年2月28日前发布的裁判文书进行统计非法经营罪案件:2014年一审72起、二审7起,2015年一审44起、二审4起,2016年一审28起、二审7起。非法经营罪在植物新品种领域频繁适用,且“久占花魁”,比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商标犯罪等各项之和还多——2014年上述三项罪名一审共计43起,2015年一审共计23起,2016年一审共计23起。
(1)有罪普遍化,涉植物新品种的非法经营案,人民法院大都作有罪判决,仅有(2014)九刑初字第39号一审判决被告人无罪和(2015)张中刑终字第135号案二审改判无罪,另有案件实质上认定非法经营罪不成立而成立他罪的(2015)双刑初字第128号案[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在不具备经营资质的条件下经营种子,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大厅有工商营业执照,符合有关法律关于经营不分装种子的资质,其在经营期限内经营不分装种子的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公诉机关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被告人经营的种子是否属于不再分装的种子。现有证据无法确实、充分的证明被告人犯有非法经营罪。]。
(2)轻刑常态化,涉植物新品种的非法经营案,人民法院大都判处较轻刑罚,以缓刑适用最为普遍,如(2015)驿刑初字第390号案,法院判决被告人夏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又如(2014)武凉刑初字第373号案一审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二审(2014)武中刑终字第125号改判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3)罚金贯彻化, 涉植物新品种的非法经营案,人民法院彻底贯彻经济惩罚,以并处罚金为主,单处罚金情形仅有(2016)甘0602刑初398号案、(2015)甘刑初字第349号案、(2014)玉刑初字第150号案、(2014)玉刑初字第193号案、(2014)甘刑初字第300号案5起。如(2014)本县刑初字第00277号、(2016)辽05刑终3号案并处罚金二千七百万元。
(4)扣押没收化,涉植物新品种的非法经营案,人民法院发现有扣押财务和种子的多进行没收。如(2014)原刑初字第311号案,法院判决将被告人周某甲涉案被扣押价值233085元的玉米种子及生产种子助剂机2台、装卸机1台、拌种机1台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2014)原刑初字第311号]
实务中主要将无证生产、销售授权品种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做处理:如杨某某生产、销售授权品种案[ (2014)武凉刑初字第373号、(2014)武中刑终字第125号:被告人杨某在没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先后与有经营许可证的种业公司以签订委托合同的形式以上述公司的名义先后与武威市凉州区等村组签订繁育“隆平206”等玉米杂交种子,并借用兴盛公司车皮计划、奔马公司植物检疫证,以个人名义将价值646.035元玉米种子销售给了河南的郝某元、河北的张某乙、四川的苏某某、山东的战某某等获取非法利益。],曹某某加工包装销售授权品种案,[(2014)原刑初字第215号被告人曹某某没取得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加工包装成京研916、农大207对外销售,经鉴定实际为郑单958。]苏某某、尚某某收购授权品种销售案[ (2013)武凉刑初字第307号、(2014)武中刑终字第34号:苏某某、尚某某均无种子经营许可证,苏某某收购凉州区永丰镇沿沟村二组、长城乡新庄村农户玉米种子后分别向褚某某等人进行了销售,构成非法经营罪。] 。也有一部分以授权品种对外销售的认定非法经营罪的,如刘某某以授权品种名称销售自行加工包装的其他种子案[ (2014)鄂钟祥刑初字第00204号:告人刘某某雇请人员在自己家中将收购来的中黄13等大豆种进行筛选、加工、包装成好日子公司名义生产的中黄57、徐豆13等五个品种对外销售],尤某某国旺以授权的授权品种名称销售其他种子案[ (2013)甘刑初字第307号、(2014)张中刑终字第36号:尤某某对外销售宣称是“先玉696”的玉米品种,但经检验不是,非法经营数额达118万元]。非法经营罪在植物新品种领域的扩张适用具体表现如下:
1、无生产经营许可证,加工包装的繁殖材料经鉴定与标注的品种名称不符。如(2014)原刑初字第215号案,被告人曹某某在没取得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在郑州及新乡等地非法加工自己命名的京研916、农大207玉米种子,并对外销售186080元,经检测所售种子与郑单958相同或极近似,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原刑初字第215号]。
2、无生产经营许可证,收购授权品种繁殖材料后进行销售。如(2013)武凉刑初字第307号、(2014)武中刑终字第34号案,被告人苏某某、尚某某收购的先玉335玉米果穗后向外销售,苏某某销售金额31万元,尚某某销售金额14.02万元,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3)武凉刑初字第307号、(2014)武中刑终字第34号、]。
3、无生产经营许可证,以授权品种名称销售非授权品种种子。前者如2013)甘刑初字第307号、(2014)张中刑终字第36号案,尤国旺发给这两家公司的玉米种子,尤国旺说是“先玉696”的品种,但这两家公司收到货后经检验不是,非法经营数额达1180375元,尚欠59户农户70余万元制种款经济损失,严重扰乱了种子生产经营市场秩序,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刑。[ (2013)甘刑初字第307号、(2014)张中刑终字第36号]
4、无生产经营许可证,购入散籽假冒授权品种销售或者以授权品种名称的数字简称对外销售。前者如(2014)阿左刑二初字第24号、(2014)阿刑二终字第6号案,马保云从甘肃省酒泉市农户手中以每公斤8元收购玉米散种子,之后假冒为先玉335玉米种子向农户出售金额较大,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阿左刑二初字第24号、(2014)阿刑二终字第6号、]。后者如(2014)酒肃刑初字第11号案,被告人马某甲与贾某甲经商议,被告人马某甲替贾某甲发运“508”、“128”等玉米种子四次,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酒肃刑初字第11号]
5、无生产经营许可证,租借别的企业资质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来销售。如(2014)武凉刑初字第373号、(2014)武中刑终字第125号案,被告人杨某在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情况下,先后挂靠农利达公司、昌农公司,在凉州区永昌镇非法繁育玉米杂交种子后,借用兴盛公司车皮计划、奔马公司植物检疫证,先后向河南、河北、四川、山东销售玉米杂交种子“良玉88”、“武科2号”、“隆平206”等,共计646.035万元,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武凉刑初字第373号、(2014)武中刑终字第125号]。又如(2014)凉刑初字第337号案,被告人贾某在自己无制种资质和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租赁张掖市甘州区乌江镇管寨村村委会的土地非法种植玉米制种“隆平206”,后收获种子35吨。经他人介绍贾某又将该玉米种子销售给安徽省宿州市商人李某,该玉米种子在运输途中被武威市农业执法支队查扣,并扣押赃款196000元,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凉刑初字第337号]
6、无生产经营许可证,委托农民生产授权品种繁殖材料未收购或未完成收购。如(2014)临刑初字第39号、(2014)张中刑终字第94号案,被告人朱某在无玉米杂交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与临泽县沙河镇新丰村二、三、七、八社联系生产玉米杂交种子,与二、三社社长签订《农作物种子生产合同》,与七、八社社长口头约定后,将种子亲本发放给农户,种植“郑单958”、“先玉335”、“武科2号”和“M13”四种种子,制种面积1000多亩。同年9月种子成熟后,被告人从四个社农户处收购鲜穗796300公斤,被告人朱某违反法律规定,在没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组织农户进行玉米种子生产,扰乱种子生产经营的市场秩序,导致沙河镇新丰村农户一千多亩土地当年收益损失,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临刑初字第39号、(2014)张中刑终字第94号]又如(2014)临刑初字第75号案,被告人郭某某在未取得玉米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与临泽县沙河镇新丰村五社农户联系生产玉米种子,通过和制种农户协商,在新丰村五社落实玉米制种面积260亩。玉米种子成熟后,郭某某从新丰村五社制种农户处收购玉米种子“郑单958”88215公斤、“先玉335”207070公斤,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临刑初字第75号、]
7、无生产经营许可证,加工包装购入的种子以授权品种名称销售。如(2014)公刑初字第436号案,被告人在自家用买来的玉米种子及袋皮,装袋加工成“良玉99号”玉米种子后分两次以每袋45元钱的价格销售给代印1500袋计67500元,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公刑初字第436号]。又如(2014)原刑初字第311号案,被告人周某甲,在租赁的仓库内非法加工泰玉2号、费玉3号、濮单6号等玉米种子,并通过物流公司销售438765元构成非法经营罪。
8、无生产经营许可证,自行繁殖授权品种对外销售。如(2014)梨刑初字第412号案,被告人冷某某在没有种子经营许可的情况下将在新疆玛纳斯县私自繁育的先玉335玉米种子和先玉696玉米种子约90余吨,销售给梨树县十家堡镇的贾某某,总金额约40余万元,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梨刑初字第412号]
9、无生产经营许可证,收购授权品种后加工分装成其他授权品种。如(2014)鄂钟祥刑初字第00204号案,被告人刘某某在夏邑县的多家农户中收购了中黄13、徐豆9大豆种,共计7万余斤。后以好日子公司名义制作了中黄38、中豆36、中黄57、徐豆19、徐豆13等五个品种的大豆种外包装袋及内标签,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鄂钟祥刑初字第00204号]又如(2015)滑刑初字第99号案,被告人刘某某在滑县新区百得公司院内,雇佣工人将繁育的“中麦895”按种子加工、包装,并同时加工包装“豫农035”、“豫农012”,意图作为小麦种子在市场上销售,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5)滑刑初字第99号]
10、将无生产经营许可证,销售伪劣产品罪以非法经营罪打击。如(2014)公刑初字第271号案,被告人曲某某在未取得品种权人授权的情况下,将吉单27玉米种子以10元一斤的价格转卖给高某某,在办理物流配送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玉米种子全部被扣押。经检验:吉单27玉米种子纯度为92%。经鉴定,一万斤吉单27玉米种子价值人民币10万元,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4)公刑初字第271号]
11、将无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涉嫌生产伪劣产品罪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如(2015)驿刑初字第390号案,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夏某某虽不具有销售种子资质,但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夏某某的行为虽然符合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构成要件,但根据法律规定,被告人的行为既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又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故应依照非法经营罪对被告人夏某某定罪处罚。[ (2015)驿刑初字第390号]
非法经营罪在植物新品种领域扩张适用,既有品种权无刑事罪名的可选替代物之实,也有行政部门治理“滥用”之意和品种权人维权“报复”,其在回应品种乱象治理的主观需求的同时,更有司法裁判诉讼便利之求,非法经营罪的扩张适用客观上也有意或无意地遮蔽或异化了品种权刑事立法保护的客观需求。
我国种子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了假冒授权品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并没有哪一条款对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行为进行定罪量刑。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对植物新品种权暂无直接的刑事追究罪名。由于刑法未明确规定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的罪名,司法实践中,仅有部分品种侵权隐藏在种子概念下寻得了诸如假冒注册商标罪、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罪、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生产销售伪劣种子罪、非法经营罪等部分刑事保护[ 见拙作:品种权二元属性实证研究,未发表。],大量的有经营资质者生产销售符合品质衡量准则的授权品种的侵犯权利的行为游离在刑事法律规制之外,相关人大代表[ 应将侵犯植物品种权罪入刑,农民日报2016年3月7日第008版现代种业周刊;]、政协委员[ 打击套牌侵权应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罪”入刑,农民日报2015年3月16日第06版现代种业周刊],以及执法机关[ 吴晓玲、彭钊、贺利云:从法律层面解决打击侵权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困境的思考,载《中国种业》2015年第9期。]和部分学者[ 杨延超:我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载法学论坛 2007 年第5 期。李秀丽:405页]呼吁增设品种权刑事罪名即是证明。
非法经营罪“几乎汇集了所有与刑法明确性相悖的立法方式”[ 见陈兴良:《刑法的明确性问题:以〈刑法〉第225 条第4 项为例的分析》,《中国法学》2011 年第4 期,第120 页。],既有空白罪状——违反国家规定,又有罪量要素——情节严重,同时还有兜底行为方式和行为方法。从《刑法》第225 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来看,采用的是明文列举的方式,对非法经营行为加以描述。但是,在前三项中,除第3 项以外,前2 项都包含着“其他……”这样一种措词,表明其对非法经营行为的描述是不周延的,可以由司法机关随时续造。当然,其续造的行为性质受法律规定的限制。例如,第1 项的“其他”只限于限制买卖物品,而第2 项的“其他”只限于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因此,这是一种有限度的续造。从明确性的角度来说,是一种相对明确。第4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是一种完全的概然性规定,对非法经营罪起到一种兜底作用,“犯罪的认定权被慷慨地散发到刑法之外”。兜底性条款的保留,使得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圈具有相当的弹性,它似乎是在顽强地继承着前辈的遗志:誓做一只笼罩经济社会每个方面、可以每时每刻打开装货的“小口袋”。如何理解该兜底条款或堵截条款,立法机关指出:“这是针对真实的生活中非法经营犯罪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所作的概括性规定,这里所说的其他非法经营行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这种行为发生在经营活动中,主要是生产、流通领域。(2) 这种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3) 具有社会危害性,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全国人工委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上述规定虽然对认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提供了一般原则,但具体如何认定,任旧存在很大的裁量空间,足以出入人罪。由“投机倒把罪”分解而来的非法经营罪,天生就有扩张的秉性[莫洪宪、罗钢:非法经营罪司法解释再解读——以城市违法建设出售行为为例,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年第11期。]。上述粗疏的立法技术导致指引规范的失调状态和行为类型的空洞现象,为日后非法经营罪的逐步口袋化埋下了伏笔。[葛恒浩:非法经营罪口袋化的成因与出路,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4期。]
令刑事司法在经济犯罪面前陷入不应有的“不作为”或“机能萎缩”,从而不仅不是预防犯罪,反而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放纵乃至助长经济犯罪[马荣春:经济犯罪罪状的设计与解释, 《东方法学》2013年第5期,第66页。]。但“法律不是嘲笑的对象”[张明楷著《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倘若司法人员运用合理的解释方法能确定该堵截条款所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的具体性质,那么至少从罪刑法定主义的角度来说仍旧能认为这一条款是明确的。然而, 刑法条文中兜底性条款、概括性条款不是口袋罪滋生的唯一“空间”,通过消除兜底性条款、概括性条款解决口袋罪的“滋生空间”以消除非法经营罪的现象并不现实。[于志刚: 口袋罪的时代变迁、当前乱象与消减思路, 《法学家》2013年第3期, 第76页。]将司法实践中非法经营罪构成要件的异化归结于立法规定的过于抽象,仅是一种虚假的表象性认识。非法经营罪的异化之过,应转向与立法规定相对应的司法过程中去寻找,在适用中司法人员对堵截条款的曲解才是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的实质[ 武良军::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之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5期]。实践中非法经营罪异化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在于非法经营罪诉讼上的便利。这种便利一方面体现在非法经营罪的证据要求相对简单,易获取,主要是证明经营行为的违法;另一方面则体现在相关司法解释对非法经营罪入罪标准的规定较其他犯罪要低。[ 武良军:非法经营罪堵截条款异化之研究,《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5期]诉讼上的便利致使司法机关为规避某罪名认定的困难而选择非法经营罪,如(2015)驿刑初字第390号案中,法院将无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涉嫌生产伪劣产品罪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当解释者对法条难以得出某种解释结论时,不必攻击刑法规范的不明确, 而应反省自己是不是缺乏明确、具体的正义理念[张明楷著 《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 上) 》( 第二版)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说第3页。]。
法律社会学已经揭示,绝对的法律是一个虚构,法律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和社会相联系,不管法官愿意不愿意,它都不可避免地会卷入政治。[陈金钊著:《法律解释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页。]近年来,在国家农业部、公安部、工商总局连续开展了种子打假专项行动,且已成为一种执法常态[程琥:运动式执法的司法规制与政府有效治理,载《行政法学研究》2015年第1期。],但套牌侵犯权利的行为由明转暗,地下生产销售套牌侵权种子依然猖獗。此种集中整治、专项治理的运动执法背景下,西北育种基地政府基于政绩和农民利益等考虑开始了磨刀霍霍杀向种子“非法经营”者突进的现象。据农业部行政执法领导曾披露,2014年张掖市农业局向公安局移送违法制种案件49起,公安局立案44起,以非法经营罪移送检察院28起,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19起,法院按非法经营罪判决10起。之所以适用非法经营罪,根本原因是当地政府主要领导为整治近年来张掖玉米基地制种乱象而采取的强力措施[ 吴晓玲、彭钊等:从法律层面解决打击侵权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困境的思考,载《中国种业》2015年第9期。]。相关案件对此也有体现,如(2015)双刑初字第128号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在不具备经营资质的条件下经营种子。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大康种业直销大厅有工商营业执照,符合有关法律关于经营不分装种子的资质,其在经营期限内经营不分装种子的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公诉机关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被告人康祥、康德亮经营的种子是否属于不再分装的种子。现有证据无法确实、充分的证明被告人康祥、康德亮犯有非法经营罪。
培育一个新品种时间长,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因繁材材料本身可自我复制,侵权容易获利巨大,加之对调查取证难,诉讼成本高,部分权利人出于取证需要而启动刑事程序,借助刑事介入把侵权事实固定下来,以推进后面的民事诉讼索赔;部分权利人是在民事救济失利之后转向刑事救济;更不可思议的是少数权利人希望能够通过刑事手段对竞争对手的经营产生干扰,增强自己的竞争优势。总之权利人在“有恶必罚”报复理念和“轻罪重罚”惩罚思绪引领下,不惜重金雇佣第三方机构调查、不计成本调动公安机关介入,不谈赔偿推动司法机关重判,由此,非法经营行为机器插上了飞翔的翅膀,高速驶入刑事追责区。
非法经营罪在植物新品种领域扩张适用,有没有合法的论证基础。一般认为非法经营罪的法定构造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于志强、郭旨龙:“违反国家规定”的时代困境与未来方向,载《江汉论坛》2015年第6期。]下面从如下几个维度进行梳理分析:
刑法第96条明确规定 “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所以,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行为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从而是否构成犯罪的依据。按照上述规定,分析植物新品种领域的非法经营,所对应的“国家法律规定”就是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种子法第9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第40条假冒授权品种,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种子法规定,主要有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但农民个人自繁自用常规种子有剩余的在当地集贸市场出售串换、以及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和受有生产许可证的经营者书面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是例外。如(2014)武凉刑初字第373号案,被告人杨某在明知自己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情况下,未经许可先后非法销售国家特许专营的玉米种子646.035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属情节很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予刑罚。但被告人杨某向辽宁销售412.16万元的玉米种子因委托繁制合同系昌农公司和农利达公司与金刚公司签订,销售系委托销售,故该笔销售金额不予认定,被告人杨某非法经营的数额应认定为646.035万元。又如(2015)双刑初字第128号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康祥、康德亮在不具备经营资质的条件下经营种子,现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康德亮的大康种业直销大厅有工商营业执照,符合有关法律关于经营不分装种子的资质,其在经营期限内经营不分装种子的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公诉机关提交的现有证据不能确定被告人康祥、康德亮经营的种子是否属于不再分装的种子。现有证据无法确实、充分的证明被告人康祥、康德亮犯有非法经营罪。[(2015)双刑初字第128号]但需要说明的是,营业执照并非免责充分条件,如(2016)甘07刑终15号案,法院认为上诉人所在公司虽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可以生产经营常规种子,但由于未取得农、林主管部门审核核发的主要农作物经营许可证,故无权生产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其在2年间明知无证生产违法,仍无证生产、经营玉米杂交种子,种植培养面积5395.92亩,收购种子产量3284036.5公斤,货值金额达7618948.30元,严重扰乱了主要农作物杂交种子市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符合法律规定。如何在司法中对非法经营罪扩张适用加以限制,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了《关于准确理解和适用刑法中“国家规定”的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规定,“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规定的‘其它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有关司法解释未作明确规定的,应当作为法律适用问题,逐级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显然,该《通知》以“逐级请示”的形式来限制地方法院对非法经营罪扩张与异化,但基层法院至今似乎并没有逐级请示的非法经营案件向外披露。
根据刑法第225条之规定,非法经营罪是违反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即构成本罪是有非法经营行为,而且必须要达到“情节严重”。如(2015)甘刑初字第349号案,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武俊庆不具备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的资质,与龙渠乡新胜村六社社长商量种植玉米种子,在口头与张某某达成初步意向后既开始落实制种面积,并于4月26日向达成意向意见的新胜村一、六社农户发放父本、母本进行种植,在村委会、乡政府的干预下于4月28日停止制种并撤离人员。其行为虽然及时停止,没有继续发展,但没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而非法生产玉米种子的事实慢慢的开始,并已付诸实施。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非法经营罪[ (2015)甘刑初字第349号];二审中(2015)张中刑终字第135号案,上诉人在没有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就擅自在新胜村一社、六社发放玉米制种种子并进行生产,属于非法经营。但生产玉米种子属于一个周期过程,一定得完成下种、田间管理、收种等环节才能完成,而本案中新胜村一社、六社于4月27日开始点种,4月28日武俊庆就撤离了技术人员,一社已全部由神舟绿鹏种业改种,六社的全部转为商业大田玉米,本案没有产生实际货物,所以没办法计算非法经营额,也没有非法所得,故就未达到非法经营罪规定的情节严重,武俊庆的非法经营行为不构成犯罪。一审法院认定没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而非法生产玉米种子的事实慢慢的开始,并已付诸实施就构成非法经营罪系法律适用错误。[ (2015)张中刑终字第135号]
《种子法》的规定,种子经营实行许可制度,主要农作物的种子实行生产许可制度,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如(2016)苏09刑终269号案,被告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明确指称案涉水稻种子并非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认定构成非法经营罪没有法律依据,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法院则认为,水稻是《种子法》规定的主要农作物之一,《种子法》规定主要农作物的种子实行生产许可制度,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无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上诉人均未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种子经营许可证》,也没获得有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资格企业的授权或者委托,未经科丰公司授权,以该公司名义与罗某某等人签订杂交水稻委托制种合同,并约定收购他人承制的合格种子,属于未经许可生产经营主要农作物种子。且经营种子价值人民币469155元,超过立案追诉标准,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又如(2016)甘0722刑初78号案,一审认定在非法制种过程中,魏某某提供亲本种子及部分前期投入款,并派技术人员指导制种,被告人权某某提供土地,负责具体制种事宜,二被告人违反法律规定,在没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生产玉米种子,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且均系主犯,应依法惩处。被告人权某某上诉称:上诉人权某某不是非法经营的主体;一审法院认定“权某某明知其与魏某某均没有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资质而生产制种玉米,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系认定错误;对上诉人权某某追究刑事责任显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宣告上诉人权某某无罪,确保无罪的人不受追究,保护上诉人正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二审(2016)甘07刑终100号法院认为,国家为保护和合理规划利用种质资源,规范种子生产经营和管理行为,维护种子生产经营者、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种子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加强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规范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秩序,实行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种子法》、农业部《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经营种子的,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种子生产经营,是指种植、采收、干燥、销售等活动,种子生产是指制种的种植、田间生产采收活动。上诉人权某某、原审被告人魏某某违反国家相关种子管理法律和法规规定,在没有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生产玉米杂交种子,扰乱玉米种子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在实施非法生产经营过程中,原审被告人魏某某提供亲本种子及部分前期投入款,派技术人员指导制种,上诉人权某某提供土地,负责田间生产事宜,二人互相协作分工配合,作用相当。该案系一般犯罪主体,二人的行为已严重违反种子管理法律和法规,构成犯罪均应依照法律来追究刑事责任。(2016)苏1324刑初659号案更为明确,法院直接认定被告人宋某某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类似适用刑法225条第(一)项案件有:(2015)响刑二初字第00028号案、(2015)高刑初字第80号案、(2015)甘刑初字第454号、(2016)甘07刑终39号、(2016)甘0724刑初11号、(2016)苏1324刑初659号、(2015)甘刑重字第3号、(2016)甘07刑终43号、(2016)豫07刑终33号。
最高法认为,刑法第225条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规定中,第四项“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是在前三项规定明确列举的三类非法经营行为具体情形的基础上,规定的一个兜底性条款,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该项规定应当特别慎重,相关行为需有法律、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且要具备与前三项规定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严格避免将一般的行政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当作刑事犯罪来处理。也就说最高法院对于第(四)项适用是持警惕态度的,但实际判决并非慎重或者限制第(四)项的适用。如(2016)甘0321刑初55号案,被告人杜德寿从武威市富民种业有限责任公司获取“隆平206”玉米亲本种子2000余斤。2015年春,被告人杜德寿产生用“隆平206”亲本种子进行制种的想法,在未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的情况下,找到在永昌县沙金园艺场承包耕地的种植户杨某某,提出由其提供玉米亲本种子让杨某某种植。杨某某同意后,被告人杜德寿向其提供价值17000元、约2100斤的“隆平206”玉米亲本种子及40000元前期投入资金,并约定以每亩2400元的保底价格收购,前期投资及亲本种子款在杂交玉米收购时予以扣除。当年春天,杨某某在沙金园艺场承包地上种植“隆平206”杂交玉米167亩,并于当年9月收获湿玉米果穗141.3吨。金昌市、永昌县种子管理站在玉米种子生产基地专项检查中,发现永昌县沙金园艺场存在涉及嫌疑违反法律生产玉米种子的情况。永昌县农牧局对该案立案审查。期间,被告人杜德寿以每公斤2.5元的价格从杨某某处收购玉米果穗58.3吨,价值145750元。之后因担心被执法人员查获,被告人杜德寿将收购的玉米果穗拉运至民勤县光明村附近空地堆放,也未再继续收购杨某某剩余的玉米果穗。杨某某将剩余玉米果穗83吨以每公斤2.8元的价格销售给甘肃三洋金源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得款232400元。被告人杜德寿拉运至民勤县的玉米果穗因无人看管致部分遗失,剩余2995公斤被永昌县农业行政执法大队查获并随案移交永昌县公安局,永昌县公安局侦查人员将扣押玉米果穗依法变卖得款3594元。经河南省依斯特种子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检验,从杨某某种植基地抽取的玉米种子样品所检项符合GB4404.1-2008规定要求,样品电泳谱带与“隆平206”谱带比对一致,该样品为“隆平206”玉米种子。综上所述,被告人杜德寿未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非法生产“隆平206”玉米杂交种子,经营数额共计378150元。被告人杜德寿违反国家规定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制度,在未取得主要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生产玉米杂交种子,情节严重,其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管理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构成非法经营罪。又如(2015)南刑初字第32号案,被告人王志信于2011年10月27日成立濮阳市华兴种业有限公司,营业范围为包装种子销售。王志信在企业成立后,明知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不能从事小麦种子收购、繁育、销售的情况下,而以该公司名义主要是做小麦种子的收购及销售活动;并雇佣被告人张某某负责田间管理、质量检验等活动。二被告人以1.16元/斤至1.37元/斤不等的价格收购小麦共计2700923斤,折合3484190元。后向武某某等人进行销售。现尚有部分小麦种子款未支付。法院认为,华兴公司成立后,违反国家关于种子管理的规定,在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主要是做非法经营小麦种子,扰乱市场秩序,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类似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 “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规定的还有(2015)青再字第0001号、(2014)本县刑初字第00277号、(2016)辽05刑终3号、(2014)青刑初字第0596号、(2015)五刑初字第2号、(2014)甘刑初字第433号、(2015)岱刑初字第12号、(2016)津01刑终426号、(2014)甘刑初字第300号、(2014)克刑初字第74号、(2014)甘刑初字第318号、(2014)甘刑初字第313号、(2014)富刑初字第28号、(2014)富刑初字第55号等。当然,有些案件是以适用刑法第225条而实际认定第四项的,如(2015)凉刑初字第192号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扰乱市场秩序,在没有种子生产、经营资质的情况下,组织农户制种,情节严重,其行为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之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法律规定,未取得玉米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而违法从事种子的生产、经营(冒用武威市某某种业公司的名义在武威市凉州区双城镇达桐村2组、7组、9组落实种制面积1300余亩进行玉米制种,秋后收湿果穗玉米种子1300880斤,价值2731848元。王某某付农户制种款1805726元,尚欠农户制种款926122元),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予刑罚。
种子法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无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或者违反种子生产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禁止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然而根本无证和违反证之规定在质上是有较大区别的,其在刑事责任追究上似要进行适当的区分为佳。从条文含义上看伪造、变造、买卖、租借证件似乎具有同等法律价位,不宜区别对待。如(2014)武中刑终字第125号案,上诉人杨某在没有种子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先后与有经营许可证的农利达公司和昌农公司以签订委托合同的形式以上述二公司的名义先后与村组签订繁育“良玉88”、“武科2号”、“隆平206”玉米杂交种子,并借用兴盛公司车皮计划、奔马公司植物检疫证,以个人名义将价值646.035元玉米种子自行销售给了河南、河北、四川、山东等获取非法利益。案发后上诉人已全部付清了制种农户的种子款。上诉人杨某没有种子经营许可资质,采取与有经营许可资质的种业公司签订委托合同,向种业公司交纳管理费,自负盈亏的方式生产经营种子,其实质是租借经营公司资质,其行为扰乱市场秩序,且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予刑罚。上诉人在生产、销售种子前,虽与有经营资质的种业公司成立委托关系,但从委托关系的内容看,该委托关系实质是双方合谋以有偿方式允许上诉人个人以有许可证的种子公司的名义经营种子,该行为实质是为法律所禁止的租借种子许可证的行为。如允许以该种方式经营种子,法律所设立的种子许可证制度将丧失意义。上诉人以委托关系为名,生产、销售种子,不能产生合法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效果,不能改变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而生产、经营种子的实质,故上诉人生产、经营种子,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应属非法经营,构成非法经营罪。但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对于租借生产经营许可证案件是否适用刑法225条第(二)规定的“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情形呢?这要进一步研究的。
也许裁判文本最能体现线号案,法院认为被告人邵某非法经营的数额已超过立案追诉标准,其行为严重扰乱种子生产、经营的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邵某非法生产的玉米种子因质量不合格以商品玉米销售,并已全部兑付了农民的种子款,降低了社会危害性,可酌情从轻处罚。所谓大批量的非法经营罪案件,主要在于农民种子款成了问题。司法应彰显良知,守住刑法底线。不能让经营违约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进行治理,那是对人权和社会的伤害。如(2014)九刑初字第39号公诉机关先是指控被告人王某犯销售伪劣种子罪,后变更指控被告人王某犯非法经营罪。被告人王某在未取得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的前提下,被告人非法将10970公斤红小豆种子以每公斤20元的价格,销售给荣军农场70名种植户使用,播种面积达311.5公顷,给种植户造成重大损失。法院最终认为,被告人王某以天津正通国贸有限公司名义与黑龙江省荣军农场签订合同的目的是通过给荣军农场提供种子,回收农产品。被告人王某提供种子的行为不是经营行为,应视为其与农场的合作行为,被告人王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犯非法经营罪罪名不成立。二审(2015)垦刑终字第50号 法院认为,王文向与荣军农场提供红小豆种子的目的是通过荣军农场种植红小豆,回收红小豆产品,双方是合作伙伴关系,种子价款为产品回收及种子质量的保证金,王文主观上没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王文及其辩护人关于王文与荣军农场签订的合同合法,王文提供种子的行为是为了履行合同,不是非法经营种子意见,符合法律规定,应予采纳。
我国已经迈入了“修法时代”[ 参见傅达林:《“修法时代”更需问计于民》,载《法制日报》2008年8月29日。],“刑法修正案”则是当下刑事立法的主要形式。刑法立法已成为中国立法活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一个方面。这种积极的立法不仅表现为立法活动的频繁,还表现在立法的内容的取向,在历次对刑法的修改中,绝大多数都是增加罪名或加重对某些犯罪的刑罚。种子法已经过新修,再修需要时日,当前修订植物新品种权保护条例呼声较高,是否通过刑法修正案之外,对于品种刑事罪名的缺口再开刑法追责之例,需要各界警惕。毕竟,刑法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它的适用往往关涉公民最核心的利益,正因如此,刑事立法更应该严谨、理性,并排除任何不必要的干扰。[刘宪权: 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立法需要依赖生活经验,但又不能全受经验支配,是因为立法需要仔细考虑生活经验的多变,立法不能钳制法官对不同个案事实作价值判断。[林东茂: 《一个知识论上的刑法学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5 页]作者觉得,刑法系最后手段,自身应具谦抑性,即只有在民事的、行政的法律手段和措施仍不足以抗制时,才能通过刑事立法将其规定为犯罪,而新品种是授权繁材和授权品名的统一,品种权兼具创造性成果和商业性标识二元属性,其中繁材对应的智力成果属于技术性的权利,仅是推定有效性,且多涉农民利益,无论是适用非法经营罪还是增设新罪都不合适。
从现有刑事立法的变化轨迹来看,大多数表现了如下特征:其一,刑事立法的修改以“刑法修正案”为主要形式。其二,刑法修订的频繁性突出。其三,刑法修订大多以经济性犯罪的法律条款为主要内容。其四,刑事立法以扩大犯罪圈为主要特征。之前的刑法修订都是为了弥补刑事立法的缺陷而进行的“堵漏式立法”,是为了在罪名设置上完善相应的立法体系,及时克服罪名系统自身的不协调与不完善。近年来,司法实务中“面对社会转型期出现的诸多问题”,“存在着扩大适用刑法的明显倾向。大量本来属于民事法律领域的事项,竟然越来越普遍地被纳入刑事法调整的范围,使得刑法适用存在着日益严重的扩大化趋势”,刑事立法上过多的犯罪化,在司法实践中入罪化的实务倾向操作之下,必然导致犯罪圈的逐步扩大。作为最严厉的部门法——刑法,理应从属于西方的权利逻辑,赋予公民最大的自由,而不是妥协于打击犯罪之需要从而盲目地扩大犯罪圈![ 刘艳红: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载《法学》2011年第11期]“将刑法看作“自足”且“万能”的治理工具,并不间断地进行犯罪化,是国家高估了运用刑法治理社会的能力。“企图多利用刑罚权的政权是虚弱的政权”[ [日]西原春夫: 《刑法的根基与哲学》,顾肖荣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 年,第45 页。]从私权的保护角度而言,刑法的适用牵涉公民最宝贵的核心利益,其对犯罪人生命、自由的剥夺往往具有不可逆性,这要求刑法条文必须明确,而不能含糊其辞。从对公权力限制的角度而言,刑罚权属于典型的公权力,具有先天的扩张性和侵略性,如果刑法不够明确,将给予权力者过多的自由裁量空间,这非常有可能导致刑罚权的滥用。[刘宪权: 刑事立法应力戒情绪——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载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
在规范层面,要求“市场准入秩序”这一集体法益遵循法益侵害具体化原则和比例原则,严格区分程序违反法律行为和实质侵害行为,准确界分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马春晓使用他人许可证经营烟草的法教义学分析——以集体法益的分析为进路,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9期。]对刑法的过度使用和依赖,会导致人们心灵麻木与羞耻感递减,对刑罚的感受力日益减弱,最后导致刑若无刑。非法经营罪不应成为替代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管理法”。“刑法是把双刃剑,必须把刑法的负面影响限制在最小范围,这也是提高执政能力的要求。要坚持刑罚谦抑原则,将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选项,防止动辄主张动刑的泛刑法化倾向。”[ 朗胜: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谈我国行使立法的积极与谨慎,法学家2007年第5期]
刘艳红教授曾言,司法良知代表了法规范之外司法正义的实现路径,刑法底线代表了法规范之内司法正义的实现路径,二者分别从法规范的外部与内部共同发力,合力实现司法正义。[ 刘艳红:“司法无良知”抑或“刑法无底线”?——以“摆摊打气球案”入刑为视角的分析,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一行为是否有必要动用刑罚,一定要具有一定的公众认同之基础。而刑法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对这种集体意识的认同,这种认同,可以称之为公众认同。[ 刘艳红:当下中国刑事立法应当如何谦抑?——以恶意欠薪行为入罪为例之批判性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2期] “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默无言声而孜孜矻矻的伟力,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孕就的。”[ [德]卡尔·冯·萨维尼: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版,第11 页。]
总之,无论是侵权人对侵权获利的“诱惑”之醉,还是权利人对刑事追责的“偏好”之醉,也还是行政机关对违法治理的“借酒”之醉,纷纷借助司法机关对偏好便利裁决的“罪”得到几分满足,不论是真的还是假的,但醉总会醒,罪总要省,法律人还要保持适度的理性,这样才可以分得“醉”还是假“罪”。最后借用钱穆先生所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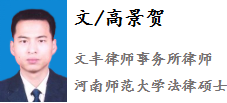
本文仅供学习参考,不构成文丰律师对有关问题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读者如有任意的毛病,应及时联系本所律师进行咨询。
Copyright © DaLv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 球王会·(体育)官方网站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高新区长江大道310号长江道壹号A座1706全国技术服务热线:400-601-0085